最新发表 |《One Earth》专题探讨复杂世界中的气候传播
编者按
距离11月联合国贝伦气候大会COP30还有四个月时间,在《巴黎协定》通过十周年之际召开的这届大会被全球赋予厚望。然而地缘政治冲突和1.5℃温控预警给这届大会增加了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Cell Press旗下国际权威期刊《One Earth》特别策划专题《打破沉默:复杂世界中的气候传播》(Unmuting the message: Climate communication in a complex world),邀请来自哈佛大学、诺丁汉大学、北京大学、布朗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德国亥姆霍兹波茨坦中心等全球高校与研究机构的8位学者共同探讨政治复杂性与气候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与互动关系,呼吁重构气候传播路径,从科学、政治、社会与文化多重维度入手,实现从“传递事实”到“构建共鸣”的转变。我院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C Force Lab发起人王彬彬受邀联合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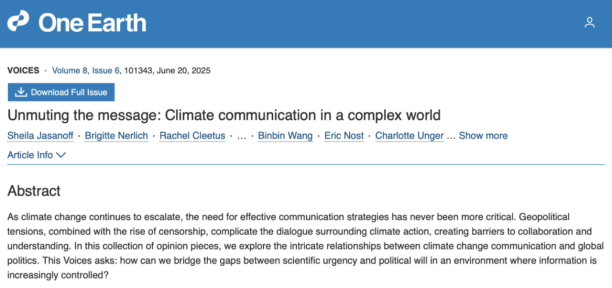
专题链接:
https://www.cell.com/one-earth/fulltext/S2590-3322(25)00169-1
核心观点:

Sheila Jasanoff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无知的社会代价
科学让我们了解自然中那些我们无法直接看见、触摸或感知的事物,比如气候变化或亚原子粒子。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将这些称为“自然种类”(natural kinds)。他称这些事物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文化或历史的产物。然而,美国现任政府显然持不同观点,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将其视为“科学觉醒主义”(scientific wokism)的体现,也就是一种可以通过删除气候相关内容和政府网站上的大量数据来从公众意识中抹去的社会历史建构。但对美国人民而言不幸的是,即美国科学界停止对气候变化及其潜在危害的研究,也并不会阻碍地球仍将继续变暖的实时。
无知只会让我们在面对风险时措手不及。明智的社会将持续投入气候科学研究,而愚昧的社会则如《圣经》寓言里那些愚拙的童女,因没有准备好灯油而无法在需要时点灯照亮前行之路。放任对气候的无知只会让我们更容易遭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如干旱、森林火灾和飓风,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与苦难。一个致力于发展人工智能的国家,竟破坏公共知识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而高质量数据正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无论是科学,还是美国人民,都理应从其领导者那里得到更好的回应。

Brigitte Nerlich
诺丁汉大学
混乱世界中的气候传播
气候变化传播在传播科学领域有着悠久的研究传统,而极端天气(归因)传播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两者的共同目标,是在气候日益不稳定的时代中,增强社区的韧性与可持续性。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颇具挑战,唯有在具备“赋权条件”(affordances)的语境中,传播活动才能真正促使人们思考并应对极端事件与气候变化。这些赋权条件包括:(1)提供有关正在发生的事件和本地风险的实用信息,以及安全建议与援助指引;(2)在紧急状况解除后,持续传递有关气候变化这一长期问题的信息;(3)谨慎使用隐喻和其他“框架设定”工具进行信息表达。然而,在当前支离破碎的政治格局中,这种本应整合的社会与传播框架正面临瓦解。此外,洪水与野火仍常被置于“对抗性隐喻”的叙述之中,例如“怪兽级洪水/大火吞噬了城镇”,将力量归因于自然本身,而非人类的活动。这种叙事方式可能强化某些政党在极端天气事件发生后依然忽视环境议题的倾向。为增强社区韧性与可持续性,可考虑以下传播策略:(1)在信息共享过程中结合有意识的隐喻塑造;(2)正视隐喻在塑造公众反应中的影响力;(3)通过实用工具与共享叙事共同构建社区韧性;(4)同时支持应急响应与长期规划;(5)在确保科学准确的同时兼顾情感共鸣。

Rachel Cleetus
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
在虚假信息泛滥的时代推进气候行动
尽管气候危机的严峻现实已不容忽视,关于气候科学的虚假信息仍在持续蔓延——其背后往往是化石燃料利益集团的操控,如今甚至已被美国政府最高层所呼应。与此同时,许多国家领导人仍执着于“零和博弈”的政策框架,将狭隘的国家利益相互对立,这与应对全球性挑战所需的集体行动与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要打破这一僵局,我们迫切需要有力、协调的传播行动,不仅要揭示失控气候变化的危险,还要强调在应对过程中所蕴含的共同机遇。那些能够与人们日常生活关切直接相连、并提供切实可行解决方案的叙事,亦是打破虚假宣传的关键所在。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气候变化都已以极端热浪、愈发猛烈的风暴、毁灭性洪水或灾难性野火的形式叩响家门。与此同时,社区还在承受海平面加速上升、超级干旱、水资源短缺和保险成本飙升等多重风险。值得警惕的是,许多对气候变化几乎没有贡献的人,却在承担着最沉重的不公平代价。这些不容置疑、触目惊心的人类与经济损失,正凸显出采取适应措施、迅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大幅推进清洁能源发展并有序淘汰化石燃料的紧迫性。
掩盖气候变化证据、打压甚至恐吓科学家,这些行为不仅危害公共利益,也必须坚决抵制。同样,那些执意扩大利润的化石能源公司也应被追责。在人类与地球未来命运系于一线的关键时刻,放弃短视、封闭、“照旧营业”的路径,转而迈向公平、转型的气候解决方案,其益处已不言而喻。

Candis Callison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讲述气候变化,需要集体性参与
如何讲述气候变化,才能让公众与政治体真正关心并采取行动,自这一议题成为全球性共识以来始终是一项核心挑战。过去,我们试图将气候变化这个模糊而不确定的未来图景加以具象化;而如今,它已频繁地与重大野火、“大气河流”等新型极端现象一起,出现在每日的新闻报道中。随着2030年的临近,我们在基础设施层面推动转型的压力与代价正迅速加剧——这正是IPCC所强调的,避免灾难性后果的关键路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提高公众意识”,而是如何同步提升公众的参与度、理解力与投入意愿,并配合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而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气候变化与基础设施的关系框架。
当下主流媒体和社会叙事中,气候变化事件往往被孤立地呈现,很少将其置于社会结构、殖民历史或资本逻辑的脉络中加以解读。然而,气候变化深刻影响并重塑着我们作为“集体存在”(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身份认知。来自北极、泰加林到南半球的多个原住民社群,正持续通过全球性协作,努力重塑对气候变化的叙事。他们不仅关心“应对之道”,更强调“我们为何会走到今天”,不断呼吁建立更加具回应性的政策体系,真正承认并纳入原住民的治理实践、知识体系与世界观。如今,由太平洋岛国原住民群体推动的一起国际法院审理案件,或许将彻底改变全球对气候变化的理解方式与应对路径。

Jennifer Hadden
布朗大学
非政府组织的双重角色:讲出真相,也激发雄心
随着全球升温控制在《巴黎协定》所设定的1.5℃目标之下的希望日益渺茫,悲观情绪正在加剧。根据《自然》杂志对IPCC作者的一项调查,仅有4%的科学家认为,到本世纪末全球变暖仍可能被控制在1.5℃以内。在这一背景下,长期倡导1.5℃目标的非政府组织(NGOs)正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这一目标正逐渐失去现实可行性;另一方面,科学与政策界部分声音也开始提出应“更新”这一目标,转向一个更具可达性的替代方案。然而,如果真正放弃1.5℃这一“黄金数字”,将显著削弱NGOs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减缓规范,也将削弱其对各国政府“问责”与“揭示失责”(name and shame)的能力。毕竟,明确的标准才构成对行为的约束基础。
在这样的局面下,NGOs能做什么?作为独立信息和政策分析的关键来源,NGOs的角色愈发重要,特别是在信息日益受控、真假难辨的传播环境中。它们不仅需要继续如实呈现科学现状,对各国实现气候目标的不足之处进行批判性审视,也应尝试扩展自身行动的工具箱,同时扮演“批判者”与“鼓励者”的双重角色。例如,面对如巴西近期在减少森林砍伐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或秘鲁在交通领域的脱碳努力,NGOs可以主动将这些进展进行放大与传播。这种传播策略不仅有助于正向激励符合气候规范的行为,还能将成功经验扩散至更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形成有助于未来政策推动的正向动能。在这个不确定性加剧的关键时刻,NGOs的“讲真话”与“激发愿景”的双重功能,或许正是重塑全球气候行动路径的关键支点。

王彬彬
北京大学
以“3C领导力”应对气候传播中的“双重叙事困境”
近年来,气候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气候工作者社群内部,有一种“双重叙事困境”:一方面过去数十年主导气候传播的是“恐吓”策略,即通过不断强调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反复聚焦全球范围内的洪水、干旱和其他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向公众传递悲观情绪为主的信息;而当我们呼吁公众参与气候行动时,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只有关灯节能、节约用水、调低空调温度、选择电动车等。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气候问题的焦虑与无力感。对此,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C Force Lab)倡导建立3C领导力,即好奇心(Curiosity)、勇气(Courage)与同理心(Compassion)。根据C Force Lab的研究,这是三个关键的心念素质和核心价值,可以帮助人们重建与内在自我、周围人和外部世界的联结,从而将人生使命重新锚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3C领导力”的引导下,科学家将更有可能走出各自的研究孤岛,主动将气候变化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联结起来,寻求协同增效,为相关利益方提供更创新和系统的解决方案。气候变化既关乎温室气体排放,更关乎人类如何在复杂社会系统中共同生存。后者是政策制定者的核心关切。因此,如果科学家能够为“科学的紧迫性”赋予更具社会广度的背景,将气候叙事从消极转向积极,那么就有可能重建希望,鼓舞更多公众采取气候行动,逐步弥合科学、政策与公众行动之间的沟通隔阂。

Eric Nost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
我们可以保存数据,但数据无法拯救我们
气候数据的掌控权掌握在对公众回应程度不一的不同机构手中。科技公司利用带有偏见的来源训练不透明的人工智能模型,并通过聊天机器人传播片面信息;威权政府则在解构数据共享机制的同时,试图打压批评者发布的数据;与此同时,诸如环境保卫基金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和ClimateTRACE等非政府组织,正日益成为气候数据收集与分析的重要力量。
我本人是“公共环境数据伙伴”(Public Environmental Data Partners)与“环境数据与治理倡议”(Environmental Data & Governance Initiative)这两个非营利组织的成员,我们致力于归档政府环境数据,以确保公众依然能够自由获取。在参与归档工作时,我始终牢记一点:政府、企业与NGO对数据的控制之所以问题重重,是因为社会变革的实现并不总依赖于“更多”或“更权威”的信息。
事实上,真正具有转变意义的气候与环境传播,往往并不依赖于科学数据本身,它更通过叙事表达,并面向情感激发(affect-oriented)。虽然“量化事实”类的数据在其中可能扮演一定角色,但它并非主要驱动力。我们也清楚,在诸如政府机构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有效利用数据面临诸多障碍,例如法律限制、资金约束与专业能力匮乏等。数据技术影响制度的过程极其缓慢,甚至可能毫无建树。同时,所谓“中立数据”本身也并不存在——这不应被视为耻辱或被回避的问题。相反,这一现实提醒我们:必须明确气候数据为谁服务、服务什么目的,将数据收集与分析纳入公民科学项目,并通过重新解构与激活现有档案,推动其服务于更具行动力与公平性的目标。

Charlotte Unger
德国亥姆霍兹波茨坦中心 (GFZ)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在“后1.5℃时代”,我们应如何谈论1.5℃目标
全球地表年均气温已连续超过一年高于工业化前水平1.5℃。这一趋势令人警觉,也带来了一个科学界与政策界都不愿正面应对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放弃1.5℃这个目标?无论答案为何,都会面临信誉受损的风险。
1.5℃虽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但本质上仍是一个政治塑造的目标。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小岛屿国家联盟”强烈推动,再加上IPCC的特别报告支持,1.5℃逐渐成为全球气候减缓行动的“黄金数字”。尽管这一数值常被解读为“安全”与“不安全”气候之间的分界线,但从气候科学角度看,短期突破1.5℃并不等同于《巴黎协定》的失败,因为该协定采用的是20至30年的长期温度均值作为评估基准。
我认为,1.5℃目标不应被放弃。目标的意义在于,将意图转化为行动的路径变得清晰可循。1.5℃不仅是判断与决策的重要参考,更是一种价值指引,有助于强化社会对哪些行为是“必要且合乎道德”的共识。即使是在“后1.5℃世界”中,它仍能作为衡量各国政府与企业责任的标尺。
然而,我们确实需要改善围绕1.5℃的传播方式。相比强调“温度极限”,我们应更多传达“每上升0.1℃都至关重要”的理念,以此凸显减缓行动永远值得付出,并鼓励从小到大的各类实际举措。同时,继续公开讨论持续升温所带来的风险也依然重要,包括许多“超调情景”在可行性与安全性上的高度不确定。突破1.5℃,不意味着我们应停止努力。归根结底,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保障所有人拥有有尊严的生活。
背景介绍
One Earth是Cell Press旗下的首本可持续发展科学旗舰期刊(1区Top,最新IF15.1),作为Cell的姊妹刊,专注于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科学,旨在弥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差距,发表高质量的研究和观点,以应对当今环境和社会挑战。

